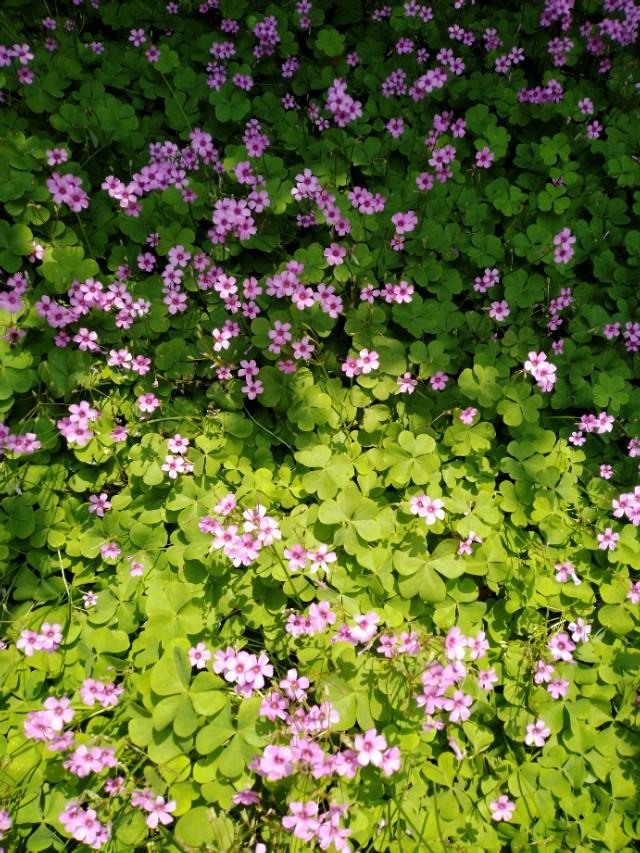最平凡的人也深不可测契诃夫短篇小说阅读有感 -凯发网娱乐
最佳答案
引:总是能在平凡中窥见伟大,地域如此,人亦如此。
一、那个不平凡的人
1860年1月29日,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中诞生了一个男孩,父亲给他取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虽然在祖父的努力下家族摆脱了最下等的农奴身份,但在属于俄国暗夜的时代,父亲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日益惨淡的经营。1876年帕维尔·叶果罗维奇·契诃夫(父亲)杂货铺破产,无奈之下举家迁居莫斯科。年仅16岁的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虽然父母没有基于小契诃夫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是夫妻二人在精神层面给契诃夫未来的成就打下了一个个坚实的钉子,帕维尔·叶果罗维奇·契诃夫对东正教十分虔诚甚至于狂热,东正教的平等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对契诃夫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虽然契诃夫从不是宗教主义者。契诃夫后来接近低层人民群众,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与悲天悯人与其父亲具有很大关系。而母亲叶夫根尼娅喜欢给几个孩子讲故事,这个本是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妇人早年跟随其父亲踏过了俄罗斯很多的土地,诸多见闻藏在肚子里,随着时间酝酿成一个个故事。俄罗斯多雪,下雪的日子最适合围在火炉边讲故事了。因为母亲的原因,契诃夫一颗小心脏在小时候就跑出了罗斯托夫省,带着丰富的想象力跃向母亲故事里的那些土地。陪着小契诃夫长大的那片泥土地并不知道,在自己的怀抱里,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家诞生了。
不知出于哪种原因,契诃夫对于自己的童年并没有过详尽叙述。但是从他与其他作家往来的信件谈论中,从其文章的只言片语中,从其他人对契诃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来这位文豪的童年生活并不是非常如意的,甚至是悲惨。“专制和欺骗毁掉了我们的童年”契诃夫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在充斥着市侩和暴力的小民阶层生活里,小契诃夫度过了一个没有该有的童真与甜蜜的童年生活。亦或者本来富有童趣的孩子在生活的滚轮下被消弭额的一干二净,以至于后来回忆起的自己只是一个在折磨中习惯顺从的中学生。在唐·博格拉兹的回忆录中对契诃夫一家在塔甘罗格市中的描写也叙述着这个悲剧:“塔甘罗格中学,就像一个特别的劳动队,学校有一个感化班,用翻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堂练习来代替棍棒责罚。"在给作家谢格洛夫的信中契诃夫也写道:
我小时候就接受过宗教教育以及这一类的培养,例如在教堂唱圣歌朗诵使徒福音和《旧约》中的赞美诗,参加晨祷,负责在圣坛上帮忙,在钟楼上敲钟。结果怎么样呢?现在每逢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它给我的感觉总是非常阴郁。现在我不信教。您知道,当初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教堂里唱三重唱《改邪归正》或者《天使长的声音》的时候,大家都感动地看着我们,羡慕我的父母,与此同时我们却感到自己是小小的苦役犯。
濒临破产的杂货店,死气沉沉的中学,囚禁的教堂……在阴郁的环境下契诃夫困顿的生活着,但同时也造就了在压抑境遇下幽默的性格——契诃夫特属的幽默。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无论怎样的难过,这个善于讲笑话的男人总是能将它化成一个个笑话笑着过去,一如他母亲将自己的经历讲成一个个故事。仿佛在那段岁月的捶打下,一个契诃夫幽默式的模型有了它最原始的形状。
1879年契诃夫完成高中学业,并成功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在长达四年的医学理论学习中,契诃夫也开始了他的文学创造之路。虽然最开始是为一些幽默刊物撰稿,以稿费来补贴自己轻薄的生活费,但不可否认的是早期契诃夫文学已经具有一定意义的批判性。再加上俄罗斯地区长期的寒冷与沙俄时代的压抑低暗,幽默型的小说总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一定的慰藉,亦或减轻心情负担。所以契诃夫早期小说虽然价值意义不高,但可读性与传播性极好,无形中为他聚拢了一大批粉丝。大学期间契诃夫的作品,在群星荟萃的蓝色俄罗斯虽然称不上深刻幽囚,但已经能窥见文章背后的批判力度。总是能通过一个个事件的荒诞与可笑,巧妙地引起阅读者的深思,将沙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虚伪与市侩的丑陋面孔勾勒出来。在《一个文官之死》中,切尔维亚科夫因为对着文官将军打了一个喷嚏就被自己的担忧逐渐的折磨消亡在沙发上。不禁令人深思:逼死切尔维亚科夫的仅是他自己的胆小么?究其所以是对沙皇专制制度鞭挞与揭露。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欺下媚上的官场风气,一件一件的不合理造成了切尔维亚科夫在社会的重压下无法正常的喘息,即使像狗一样的卑躬屈膝着,也还是一步步的走向死亡。切尔维亚科夫的死亡在我看来反而是一种最好的解脱,离开了比死亡更让人可怖的东西——禁锢着的自由。
1844年契诃夫自莫斯科大学毕业,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与此同时,开始了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医生与作家仿佛注定有一种奇妙的共通性,毕竟医生的刀和作家的笔都是能将人剖开的东西。一次偶然的机会将所喜爱或敬仰的几位作家放在同一张纸页上,竟奇迹般的发现许多都和医生这个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医学院肄业;渡边淳一做了一辈子医生;柯南道尔曾经是一名船医;毛姆进入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习;福楼拜也曾经是一个医生。开始思寻这两个职业的同性。首先二者出发点基本相同,医生在于救人,作家在于救世。在“救”这个字眼上二者巧妙地相遇了,然后小心救人的医生变成了大气魄救世的作家。次之是二者的关注点相同,都是在思考一些古老的话题:生命,欲望,血液,繁衍等。最后就是自身敏锐的观察力与所处环境更容易使医生蜕变为一个大作家,毕竟人类在生老病死之间最能体现人性的本质,医生目睹过人的出生,也目睹了人的死亡。这个小轮回除了医生这一特殊职业再也没有人能在不再主动探究的情况下了解很深。冯唐说:“医生每天面对着病人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病症,各种各样的痛苦,每个病人表现和忍耐痛苦的方式又不同。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够感受到病人的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也是这样。写作表达的是‘人性’,人性纠结,各种苦。如果说作家与医生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我想可能是‘痛苦’”。医生缓解身体的痛苦,写作缓解人心的痛苦。所以有一个医生标签的契诃夫,更容易感受到沙俄时代人民的苦难与悲惨遭遇,同时也看到了这个社会是如何病到骨子里去的。而且最为一个医生,他能更深入到最广泛地民众阶层。在痛病与死亡面前他听到了太多了对于这个时代的控诉和叹息,一把火在这个年轻的医生身体里愈燃愈甚,最终被他倾入到了文字中。在俄罗斯总是能感受到意外的寒冷,契诃夫的这把火冻得整个俄罗斯文坛难受。
在《苦恼》中对马夫姚纳·波塔波夫的描写,在儿子死了之后他想将自己内心的苦恼同几个不同的人倾诉,但后没有得到一丝儿同情。三次不同的倾诉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无人静下心来理会一下他的悲惨。若说军人与三个青年的漠然是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阶级差异,下层阶级的人民的性命在上层阶级就好像一只猫,一只狗一般卑贱,尚可以归罪到制度上去,但同为车夫的年轻人也是无动于衷的冷漠,真的让人感到一种刺骨的寒冷。是俄罗斯冰冷的天气冻结了人性么?整个社会呈现着有骨子里散发的病态。契诃夫在描写姚纳的苦恼时候只是一如既往的冷峻诉说,但是不妨碍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我们的心:
姚纳的眼睛焦灼而痛苦地打量大街两边川流不息的人群:难道在那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连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都找不到吗?人群匆匆地来去,没人理会他和他的苦恼……那苦恼是浩大的,无边无际。要是姚纳的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的话,那苦恼仿佛会淹没全世界似的,可是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没人看见。那份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哪怕在大白天举着火把去找也找不到……
无奈之下姚纳向他的马儿,一只牲畜讲述着他的悲惨遭遇。所幸马儿没有将他最后的期望掐灭:
“是这么回事,小母马……库司玛?姚尼奇下世了……他跟我说了再会……他一下子就无缘无故死了……哪,打个比方,你生了个小崽子,你就是那小崽子的亲妈了……突然间,比方说,那小崽子跟你告别,死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小母马嚼着干草,听着,闻闻主人的手……
姚纳讲得有了劲,就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
在一场人与牲畜无形的较量中,人性败落的非常彻底。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与这些麻木冷漠的人物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当这种属于姚纳的痛苦弥漫到沙俄社会时候,就是一种悲剧了。
1886年是契诃夫发表短篇小说最多的一年,几乎达到了两日一篇的数量。但是后来却逐渐减少作品数量,将笔锋对准社会深层问题的关注,创作转向了深邃有意义的作品创作之中。巧的是这种转变不是由于某件大事件或大人物,仅仅来自于一个不起眼的名字: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德米特里是俄国一个年老作家,在阅读了契诃夫的作品后给青年契诃夫写了一份信。信中肯定了契诃夫的才华,并且希望契诃夫能够珍惜自己的才华,在思考下进行创作,写更多的太有意义的作品。在此之后,契诃夫以严肃的文学态度取缔了为谋生而创作的理念,开始成为一个纯粹的作家。而德米特里也被戏称为“著名作家”,变成了俄罗斯历史的“汪伦”。但是最平凡的人有着不平凡的意义,德米特里或许成不了俄罗斯的大文豪,不过他能读懂契诃夫,并且在最适合契诃夫的时代让他转向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走上世界文坛。
1887契诃夫由于自己身体原因去往乌克兰东旅行疗养。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契诃夫文学疗养时期。回来后他的文章就趋于严肃化了,摆脱了以滑稽幽默为主型的文学形式。开始看向自然,思考沙俄人民的命运,更深层次的思考自己创作的意义。《伤寒》《吻》《沃洛嘉》《祸事》《婚礼》《逃亡者》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第二年他的中篇小说《草原》荣获“普希金文学奖”。这既是他的文学的一次飞跃,也是他精神意志的一次飞跃。尽管这样,契诃夫还是将自己自囿于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他讽刺社会,讽刺制度,却从未走进过沙俄的政治圈子。他在1888年10月的一篇书信中就做出过庄严的声明: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论者,不是修道士,也不是旁观主义者。我倒愿意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就这么一点儿愿望而已。”他热爱公益,热爱俄国,但是他总是游离在政治结社的边缘。作为一个清醒的,拒绝顶礼膜拜的作家,他成功的坚守着自己内心的自由。
1890年契诃夫只身一人游历库页岛。作为沙俄的流放地,库页岛上遍布着地狱般的惨状。后来经过贫穷的西伯利亚,民众的苦难生活使他对沙俄黑暗的现实一个清醒的认识,一直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契诃夫消失了。反而是以一种决绝的冷血姿态向沙俄的专制制度展开了冲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契诃夫向世人展现着沙俄时代人民的悲惨。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和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因为这段经历诞生,同年,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贼》《古塞夫》等。在此之后,契诃夫文学进入了他生命中的巅峰时代:
1891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决斗》,向列夫·托尔斯泰的“勿抗恶”观点进行挑战,成为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向着托尔斯泰冲击的作家。
1892年,他创作了《跳来跳去的女人》《邻居》和《第六病室》。
1893年,他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匿名氏的故事》和《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
……
在此十年中,一部部经典在契诃夫笔下接二连三的诞生。沙俄时代的丑陋与黑暗在社会在契诃夫小说中被描述的淋漓尽致。如同一个冷漠的剑士,一次又一次向丑恶发起攻击,沉默寡言是他,冷淡无情也是他。谁能想象这是那个在十六年前给大家讲幽默故事的人呢。沙俄人民的悲惨遭遇造就了契诃夫的在泥泞境遇中飞速成长,但契诃夫未尝不是那个时代被上帝派遣的天使。被平凡的人民造就的不平凡的大文学家,他的文学与生命总会与那些挣扎在最底层的困境人民联系在一起。成长在那片困境中的剑士想努力刺破困郁的黑暗。他成功了。
1904年1月7日,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本来是意向中是喜剧的《樱桃园》,被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将全剧变成了一部悲剧,这仿佛预兆了俄罗斯文学世界将有悲剧发生。悲呼!同年7月契诃夫在巴登维勒与世长辞。被安葬回莫斯科仅仅是契诃夫的躯体,灵魂仍然还是飘荡在俄罗斯蓝色的土地上,在那片被黑暗笼罩的土地上,契诃夫以他独有的热情与爱倾注给了看到的苦难人民,冷漠刺向不合理的黑暗制度。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好像也有受到契诃夫人生的影响。阅读《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的那段日子,不禁审问自己,契诃夫真的死亡了么?
二、那些平凡的的人
“小人物”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中,随着现实主义应运而生的一类人物形象。该群体主要由平民知识分子,下层官吏,普通劳动者,无所事事的游民等构成。尽管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对小人物这一群体有过刻画,但契诃夫的小人物更有味道,他笔下的这些人更符合小人物的形体特征与语言能力。契诃夫笔触坚持着简洁与质朴,他的小说的艺术美的表现在朴素真实。当我们谈他的小说,竟是能感觉到文章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景,物,人有着高度吻合。因为他写小说从来不会去故意雕琢、粉饰、营造一些曲折离奇的情节或者冗长乏味的对话取胜,反而是最沉默式的记录手法。他仅仅想把社会最真实的样貌记录下来。契诃夫曾对谢格洛夫说:
一个作家,一定要使自己养成聚精会神、永不休止的观察力。你必须做到把优良品性的培养变成直接习惯,变成天然素质!”也多次建议库普林到第三等级里(工人、农民等被统治阶级)多走走。他对捷列绍夫说,“到一千俄里、两千俄里、三千俄里外的地方.....你们会了解很多东西,会带回很多的故事!你们会看到人民的生活,在偏远的驿站和木屋里过夜,完全像普希金时代那样……只是一定要沿着铁路到第三等级中去,到普通的民众当中去。否则,任何有意思的事你们都不会听到。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明天就买张到下诺夫哥罗德的票,从那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路走下去……
尼古拉铁路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胖子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嘴唇上粘着油而发亮,就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拿着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他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高身量的中学生,眯细一只眼睛,是他的儿子。
简单的笔触就勾勒出胖子与瘦子地位的差距。如他们吃饭之后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胖子是“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是“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再如写瘦子的瘦,不仅表现在自己瘦,连他的妻子也是个“长下巴的瘦女人”,他的儿子也瘦,是个“高身量的中学生”。通过简简单胖瘦就描绘了他们拥有财富的多少和身份的高低。甚至他们的物品,亲人都与饭后散发的气味混在了一起,和谐且曼妙着。
契诃夫认为,要是描写偷马贼,就不必作偷马是不道德的坏事之类的议论。所以小人物的深不可测并非是以卑微的地位做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也不是表现在心思的深沉,仅是完全的符合他这个人的还有的意识形态而已。在浅薄的书页上,一旦他们有了健全的人格,浑圆的形象不会囿于二维空间无思想与意识形态中,就深不可测了。胖子与瘦子就是在跳出书页给读者表演一场闹剧。在这场读者与作品的双向对话中,契诃夫给他们给予了一定的生命力。所以他笔下的小人物丑恶的真实,这些人卑躬屈膝,欺下媚上等形态表现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与语言中,并非是在一个个形容词,名词中浸泡着腐烂的躯壳。不过契诃夫式小人物里不仅是有奴性的,堕落的那一类,人性的光点也在他们身上表现着,如《万卡》中的小万卡:
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信件丢进邮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邮车,把信从邮筒里收走,响起铃铛,分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他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过了一个钟头,就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
九岁的小万卡被送到靴匠阿利亚兴的铺子里当学徒。在文中他给爷爷康斯坦丁•马卡雷奇的信中引述的回忆可以看出这三个月里,小万卡的遭遇是异常悲惨的。与其说是当学徒,不如说是当奴隶。不仅每天吃不饱饭,而且老板,老板娘因为一点儿错就要打他戳他,师傅们也在耍他,晚上还得哄老板的孩子入睡,而他自己不能睡觉。在这种境遇中万卡觉得快活不下去了,但是他并未对生活完全丧失了希望,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孩子,那点尚对世界抱有幻想的美好在思想沉沦,金欲横行的时代弥足珍贵。所以在给爷爷写信的过程中,他幻想着爷爷能带他回去,脱离这种苦难。然而一封没有地址的信,能不能到达康斯坦丁手中,文末并未交代,读者未可知,但同时也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苦恼》中的马夫姚纳·波塔波夫即使被生活压迫着,即使胸腔弥漫着儿子死了也无法诉说的苦闷,但是也依然坚强的活着,甚至在向往能好一点的生活:
“其实我连买燕麦的钱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契诃夫认为:“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是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这些小人物也许一辈子都不与大的波澜有过接触,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向往与幸福,这些向往和幸福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可笑的,但是却是他们独有的。诸如小万卡,姚纳之类的小人物,他们的深不可测在于能在万恶的世道向往美好。当他们对这个世界给予善意之后,并未得到善意的回报,甚至只有恶意,这个时候,能够不失望,才是真正的希望。在黑暗的沙俄时代,总有像万卡般的小人物散发着微弱的光芒,又正好被契诃夫捕捉在了文章中。
契诃夫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异常丰富。他并未将笔下的女性丑恶化或者是美化,只是自然的将她们生活中的模样付之于笔端而已,真实的展示了她们的原始状态。她们有纯洁也有善良,但是并未掩盖虚荣与放荡。在描写中契诃夫也揭露了沙俄时代对于女性在肉体与精神的迫害,同时也在剖析女性意识的种种缺陷,促进俄国新时代女性的诞生。一如《在峡谷中》对阿克西妮娅的描写:
阿克辛尼雅生着天真的灰眼睛,那对眼睛难得眨巴一下,她脸上老是带着天真的笑容。她那对难得眨巴的眼睛、长脖子上的小脑袋、苗条的身材,都有点蛇的样子;再加上绿色的衣服,黄色的前胸,唇边露出微笑,看上去活象春天从嫩嫩的黑麦田中挺直身子昂起头来瞧着行人的一条毒蛇。
契诃夫在描写中并未对阿克西妮娅刻意丑化,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阿克西妮娅逐渐却向一条毒蛇的性格进发着;她为了争夺家产用开水烫死了丽巴的孩子,在金钱的诱利下,这个本是善良的女孩子一步一步走向堕落,变成了一个黑暗中喘息的毒妇。这种无形的变化最是深不可测,在丽巴孩子死的那一刻,阿克西妮娅也消亡了。留存的不过是一只被利益驱使的肉体。但是契诃夫笔下的不只是向阿克西妮娅般走向堕落的女人,还有娜迦类对生活发出控诉并且反抗的人。她抛弃了寄生式,日复一日的苍白的旧生活,离家出走,奔向辽阔的,充满神秘的新生活。“整个过去已经与她割断,消失,仿佛已经烧毁,连灰烬都随风飘散了似的”在文章中,契诃夫如是写道。
小人物的深不可测在于敢于向生命发起挑战,在于能忍受生命极限的痛苦。他们同样为了生活奔波,无论善良还是庸碌,他们身上都压着一个甚至许多胆子。小人物在重担下缓缓喘气。而契诃夫将他们同担子一起写入书中,再被读者拿起,唤出书页表演。当生命再次被唤醒的那一刻,他们都是深不可测的。
撰文:毛富康